瓜叶山笋入乡梦
文/黄阿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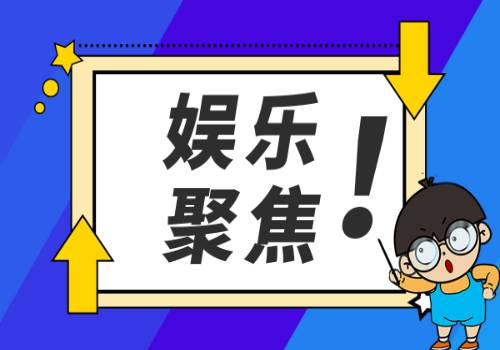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前段时间遭遇多年不见的大旱,我的心也枯焦如焚。好在近日台风骤起,普降甘霖,江河水塘又泛起了一层层柔柔的绿波,由此,我方能无愧意地对家乡涌起一遍遍温馨的回忆。记忆中,南瓜苗在坡上垄间绿色葱茏,竹笋在山间林下昂首挺立,还有这两种食材混搭汤煮在锅里沸腾翻滚的情景……
对孩提时代最深的印记,还是“艰辛”二字。生长在大石山区,十年九旱,耕地少不说还很贫瘠。家乡小屯就蜗居在山坳下,四围高山耸立,抬头仅能看到碗大的天。屯里人口少,似乎永远不到100人,往往是生了几个,当年又走了几个——出生和殁去进行反复而又惨烈的拉锯战。曾经在春旱时期,饮水困难,突然半夜雨来,我和家人一起骨碌爬起,拎水桶往水池跑,这叫“人作的卢飞快”,奋力舀水,这叫“扬手接飞瓢”;我也无数次听到半夜里从外村赶集卖柴火的乡亲们,经过我屯半山腰公路时那沉重的喘息声、响亮的吆喝声,看到一排如长蛇般蜿蜒的照明用的火把,我看到乡亲们的生活我也在发颤地想我的明天。
幸好还有瓜叶山笋菜“抚慰我心”。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,竹笋煮南瓜叶就成了一道美味,它似乎是为救世而来,一下子攫住了我们的心。青黄不接的三四月份,南瓜苗脆生生地横空出世:青绿的藤蔓,青碧的嫩叶,柔软的茎须,掐了一小把抓在手上,南瓜苗还扑簌簌地抖,仿佛还有生命在律动。剥瓜苗时,将嫩叶的茎皮一侧轻轻一摁,左右相抵,两侧一掰,即可将嫩皮剥掉。有老练者甚至能大弧度地将老瓜苗拗开,细细剥离,剥出清亮水渍样。洗时轻轻抓洗,不能肆意揉搓,这是因为瓜苗有细小的毛刺,搓过头了倒反会在吃时有毛糙感,这也显示出南瓜苗的个性:遇钢则钢,遇柔则柔。煮时也少翻动,仅在将熟时放点油盐即可,或可提前放些蒜米。但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月,哪里顾得到那些佐料?有时油料不够,放一两瓢玉米糊下去,即可将南瓜苗治得“妥妥帖帖”,温和入口了。其味清香柔和,嚼后口有回甘。印象中南瓜有几种品种,尤属细长葫芦瓜型的南瓜苗最好吃,不像现在农贸里售卖的施过化肥的瓜叶,生涩硬柴,极难下咽。
可惜南瓜苗和竹笋“联袂”的时间不久。南瓜苗盛产期应该是4、5月份,而山笋则应是在6、7月,偶合的日子比较少,而且天越旱,山笋生长期则越往后延迟。
老家山上盛产的竹子,学名可能叫方竹。不像河岸的龙头竹,枝叶盛大但茎刺极多,令人惶惶不敢靠近。家乡的方竹,茂盛中见刚强,干硬中见丰厚。一场大雨过后,春笋即破土而出,高度在20至50厘米时烹煮最佳。如果长至1米以上而人们不给竹笋尖头加上套头,极有可能被竹虫毁坏。也有乡亲认为竹笋不砍不繁殖,砍得多长得越繁茂。故有乡亲借已被竹虫咬坏的名义,砍笋而食;有人以“不斫不立”的理由,收笋果腹。其实这二者,皆可谅解。
“三夏”农忙时节,乡亲们都累成一条狗。那时我家总共有6个人,奶奶、父母和我们三兄弟,这大概是全家有史以来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;老道公“贴公”也还健在,但似乎已经90岁,走路拄着拐杖;大伯父依旧蛮硬刚直,说话时声如洪钟,只是偶尔咳嗽;几个叔叔婶婶依旧勤快麻利,劳作时热情搭话。人们在田间地头耕地,培土,盘瓜苗,忙得不亦乐乎。他们有时靠着石垄休息,看得出极其疲惫,但眼神还是那么坚毅,似乎在说“回家还有美味,慌啥”。
归家。先将笋衣剥开,露出细白洁净的笋身,将老笋根节切除,剩下的切成细长条状,焯水20分钟左右,煮出深黄色的涩水,用清水泡洗滤干,再重新下水煮,后面再放下剥好的南瓜叶同煮即可大功告成。
煮好的瓜叶竹笋菜,自有一番风韵:山笋色如白金,瓜叶青碧如玉,清白相间,这恰似人身上具有的“清白”之品质。一口下去,满嘴清香,仿佛饱啜着大自然的芬芳,如果先以猪肉煎油煮则更佳。我曾经用一首拙诗赞美:“平生挚爱只此汤,梦里朵颐仍觉香。清白两色盐加注,人间万事无一桩。”
有一回实在太饿太累,竟不知不觉间吃了五大碗,霎时大汗淋漓。我只顾脱下湿透的上衣往竹竿上挂,家人以为我“食业结束”,谁知我又返回继续狂吞,家人大笑。这叫“众人以为这厮吃饱喝足腆肚将去也,却未料其转身扭腚再折回。”
我和我的家人,以及父老乡亲们,就在南瓜苗和山笋的滋养下,度过了那段最艰难而又漫长的岁月。直到打工风潮渐起,外省务工的汇款不断寄回,家乡终于能建起楼房,饮食条件也大为改观。但不管如何,那道青白相间的瓜叶山笋菜始终是乡亲们和我的至爱。
我家的家庭建设是比较早的,但后来日子过得最艰难。因为三兄弟都读书,无人外出打工。但等到我们都毕业的时候,父亲逝去了,我们内心悲恸欲裂。父亲是一个坚韧而聪慧的人,当过电影放映员及代课老师,卖过粉,及至挖过煤。那一年,紫薯藤蔓和南瓜苗在玉米地把父亲围成了个圈儿。
再过了多年,几个叔叔陆续病逝,老道公“贴公”也走了,我的奶奶也以98岁的高龄安详西去了。家乡前方的坡地上,散布着几座令人窒息的坟茔。季羡林说:“耳畔频闻故人死,眼前但见少年多。”于我而言真是感受尤深。他们都是我的亲人,我的父老乡亲,他们的音容笑貌,宛如在昨日。想起他们,就想起当年和这些邻里之间互相蹭饭和送南瓜苗的往事。
如今欣逢盛世,人们的荤素菜蔬自然已经可以实现“选择自由”,但我还是对这道菜念念不忘,也许是因为它记录了一段我家庭的历史,也许是它道出了生活艰辛的本质。以至于在五风十雨的夏季,我就遥祝家乡的瓜苗蓬勃生长;在潇潇雨夜,我就想象竹林下山笋破土而出之喜态。这画面连同它的美味,齐齐走进我的梦中,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……